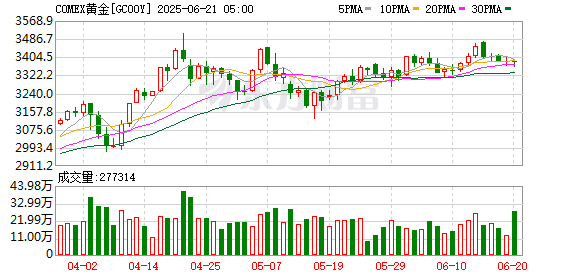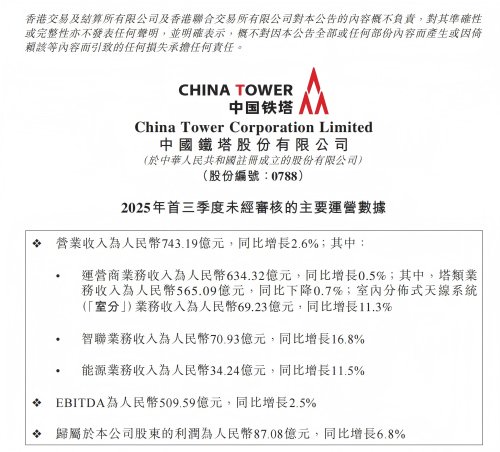智策管家 人民的抗战·陪都之屏障丨打通抗战中的交通生命线川黔公路

川黔公路渝黔段是在抗日战争全面爆发前夕的1935年开始修建的,它北起重庆,经巴县、江津,在綦江北渡场进入綦江县境智策管家,由北往南贯穿綦江全境,在安稳镇崇溪河处进入贵州。抗日期间,川黔公路与川湘公路在綦江交汇,成为战时首都重庆通往抗战前线的交通要道,起到了抗战大后方连接国际社会援华重要通道的作用,也让綦江这个川黔边境上的偏僻小县,成为陪都重庆的重要战略屏障和抗战交通线上的重要节点。
▲川黔公路九盘山路段。通讯员 张学成 摄
边测量边施工,限期赶修渝黔段
上世纪30年代初,綦江陆路交通运输主要靠人背马驮,境内虽然有一条贯穿南北连接川黔的古驿道,但年久失修,破烂不堪,通行困难;水运则因河流多为山间溪流,水急滩多,也很艰难。放眼整个四川,彼时的交通也相当落后,严重制约了全省的发展。
为了改善交通落后状况,四川省政府决定修建成都至贵州省会贵阳的川黔公路。然而由于连年灾害,军阀混战,同时因为当时四川执行的是防区制,各个防区由不同的军阀把持,政令由统治该防区的军阀所出,税费由统治该防区军阀所收,四川省政府拿不出钱来修筑公路。川黔公路在地方市、县垫资修建的情况下,只修通了成都至重庆的成渝公路,加上贵州省已经修通的贵阳到桐梓松坎路段,全线还剩下重庆至松坎的渝黔段没有建成,其中綦江境内长98公里。
展开剩余83%1935年初,国民政府中央势力以追击红军为由进入四川,为了改善四川与邻近省份交通不畅,加强对西南边陲地区控制,同时也为了建设抗击日本侵略者的后方根据地,蒋介石严令限期修通川黔公路。
▲《新蜀报》登载川黔公路修建情况。(图片来自《抗战綦江》)
据《抗战綦江》记载,1935年1月,蒋介石行营参谋团抵达重庆,提出“边测量边施工”,限期4个月修通川黔公路。国民政府军事委员会奉命修筑,饬令巴县、江津、綦江三县征集民工,工程所需的石材、木料就地取用,各地不得借故阻挠。同时指派交通部公路专家罗竞忠为工程师,限于3月底完成测量任务。
罗竞忠受命后沿以前测定的川黔铁路线,分巴县、綦江北、綦江南、江津4段定线测量。巴县、江津和綦江北段如期完成;綦江南段原测定沿綦河边的路线因为多系坚石岩层,不适合赶工,改为经东溪场,致使测量任务拖到4月12日完工。
3月,蒋介石进川,手谕国民革命第九军军长郝梦岭负责川黔公路川段修筑任务,并命令该军五十四师协同修筑。同月底成立了川黔公路川段工程处,办公地址设于重庆海棠溪。綦江成立筑路委员会,县境内划分北渡至桥河、桥河至雷神店、雷神店至盖石、盖石至东溪、东溪至岔滩、岔滩至崇溪河6个工区,每工区设大队,大队下设小队。工程的桥梁、涵洞、堡坎全部发包给建筑商承建。路基路面则征集民工自带工具、雨具包干负责限期完成,公家只管吃饭,不给报酬智策管家,占用的农田、拆迁的民房也只给很少的补偿。
▲征调民工给地方政府的训令。 (图片来自《抗战綦江》)
用时109天,筑路速度打破纪录
川黔公路渝黔段起于重庆海棠溪,过江到储奇门再到牛角沱,就连接上已经修通的成渝公路。重庆海棠溪至崇溪河段工程,巴县、江津段由于施工比较容易,于1935年5月19日完工。綦江境内路段因工程艰巨,施工艰难,北段于同年6月16日完工,南段(镇紫街至崇溪河)因为测量时路段改线延误开工时间,加上山势陡险,山崖石质坚硬,工程艰巨及民工没有按时到位(原定2万人,开工时只有1万人,民工最多时1.7万人),工程进度缓慢。
为了抢工期,尽早完成公路修建,工程方面盖石至珠滩一段原设计8米宽,改为4米宽的单行道;民工方面,除江津、巴县两段已完工的民工调至綦江工地外,还从南川调民工5200人来綦江工地。石工除催促原定江北、江津、合川、涪陵、泸县、南川、璧山、合川、长寿、钢梁、武胜等11县的1.25万人到綦江工地外,还新增宜宾、江安、南溪、大足、永川、邻水、隆昌、遂宁、潼南、荣昌、内江、富顺等14个县1万多人,增调民工均由各县派员率领赶赴綦江工地。通过种种办法,终于在6月19日勉强完工,6月20日全段通车,并在綦江县城举行了盛大的通车典礼。
川黔公路渝黔段从开工到完工用时109天,修建大小桥梁55座,堡坎27处,涵洞1186个,开挖土石方170余万方,其中綦江段有大小桥梁30座,涵洞789个,堡坎27处,占用耕地427亩。
▲《新蜀报》报道綦江等县垫资修川黔路的新闻。(图片来自《抗战綦江》)
重庆市图书馆馆藏1935年五期《新世界》杂志《川黔公路成功》一文记载:“川黔公路仅以九十七万元的开支,一百二十七万一千二百七十二民工工日,三十四万七千三百八十八个石工工日,四十二万兵工工日于一百零九日之内,完成长达一百七十六公里之康庄大道,开支经费,筑路速度,打破四川以致中国之筑路纪录……工人晴天无草履,雨天无蓑衣斗笠,寝处无稻草,晴受蒸晒,雨受泥泞,晚睡则多人堆叠,与乞丐无异。又大工程所在之工地,夜间必点气灯赶筑,工人不得片刻休息,疲惫之状,有如泥鬼。得病更无人照料,死者只得埋葬费六元而已。报酬亦极低微,民工每日只领伙食费一角二分,因米价昂贵而不得饱,有时更因食米运输不及,购买小麦蚕豆磨成粗面蒸熟充饥,亦无小菜盐巴。食时互相默视,有如难民穷蹙于异乡。工人亦未经团体训练,临时不知秩序为何物,自不能恪守规矩,是以恒遭责罚鞑答,知识不足,亦可哀也……”
据东溪、赶水一些老人回忆,修筑川黔公路占用民间房屋,土地赔偿过低,给綦江沿线百姓带来非常大的困难。重庆市档案馆所存历史档案资料记载,筑路期间,綦江受灾,百姓生活很苦,乞丐成群,一些灾民剥树皮挖草根充饥,修筑川黔公路是公家管饭,可因为粮款不济,大大影响工程进度。筑路委员会綦江段民工粮食主任张吉三万分无奈之际,向粮食商家赊来大米以资补急,直到公路修成,仍欠粮食商人米款本利共计7800.88元,因无力偿还,遭粮食商人不时追讨粮款,甚至发生扭拉经办人员跳水拼命之事件。
尽管筑路的民工艰辛,沿线百姓遭占田拆房,然而在这么短的时间内修通川黔公路重庆海棠溪至綦江崇溪河段,贯通了川黔的交通大动脉,堪称奇迹。
▲抗战期间川黔公路繁忙军运。 (图片来自《抗战綦江》)
征集民工,全面整修保通畅
川黔公路修筑时间过短,筑路任务是在国民政府强令赶工,因而修筑质量差,当时川黔公路上有3座大桥(北渡附近的綦江大桥、珠滩附近大桥及赶水的大桥),因时间过紧均未修筑,而是靠船载汽车摆渡过河,因此非常不方便。
通车几个月,一些路段因路沟不畅,雨水不能及时排出而浸泡路面,造成路面坍陷;一些路段因两旁未修护坡,泥土松动垮下阻断路面;一些路面因过窄车辆通行困难。
1936年1月,国民政府下令彻底调查并征集民工修整。据重庆图书馆藏《北洋理工专刊》中《指导修理川黔路工程工作报告》一文记载,川黔公路江津段“陷车地段颇多,申家垭口之枇杷弯,系之字形路段,坡陡弯急,须倒车方能通过”,綦江段“坡陡弯急,行车极感不便,依山沿河路段,上则土石崩塌,拥塞路面,下则斜坡护墙,倒毁不堪”,因此川黔公路车辆行走极为不便。
▲川黔公路渝黔交界处。通讯员 张学成 摄
为了彻底整修川黔公路,四川省公路局提出,江津县征工4万名,綦江县征工4万名,于1936年1月4日开工。四川公路局派出技术及管理人员,每十公里设监工一名,每县设段长一名,在綦江设工程总段,设总段长一名,计划至该年12月27日全部完成整修任务。
然而由于川湘公路亦开始动工兴建,也需征用大量民工,故而川黔公路整修工程未能按时完成。至于川黔公路上的北渡大桥、赶水大桥的修建,直至1938年2月9日,重庆行营才以行道字第758号训令,批准成立上述两桥渡工程处,负责两桥修建任务。
北渡桥渡工程处于1938年2月16日动工修建,次年1月完成通车,投资42267元。赶水处大桥于1938年2月17日动工修建,次年11月完成通车,投资22811元。两桥都是石礅钢架木板桥,仅容单车通行。
为了修筑川黔公路,綦江百姓吃了很多苦智策管家,付出了巨大牺牲,终使川黔公路建成。这条公路的修筑,极大改善了綦江的交通状况,在抗日战争中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。
发布于:北京市星火牛配资提示:文章来自网络,不代表本站观点。